除了虚构,还有结构
一
今天说“结构”。
小说除了故事,还有一个结构问题需要讨论。
一般来说,小说如果在结构上失败了,那就是一种彻底的失败。好像也有例外,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小说在结构上的冗长与拖沓,让人感到痛苦,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地位。他的小说出示了更重要的问题,使我们的阅读能轻易地越过结构本身带给我们的障碍。
这是传统小说的优势:由于作家触及了那个时代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读者往往能够原谅他在艺术上的某种疏忽。当然,艺术形式与作家的精神经验总是同构在一起的,关键在于作家的重心在哪里。如果一个作家将形式作为写作的终极目的,那么,他所建筑的艺术秩序与艺术图景便成为他世界观的全部基础;如果一个作家所看到的真实,不能通过自己建构的艺术秩序出示出来,形式便会转换成他对存在本质的探查方式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属于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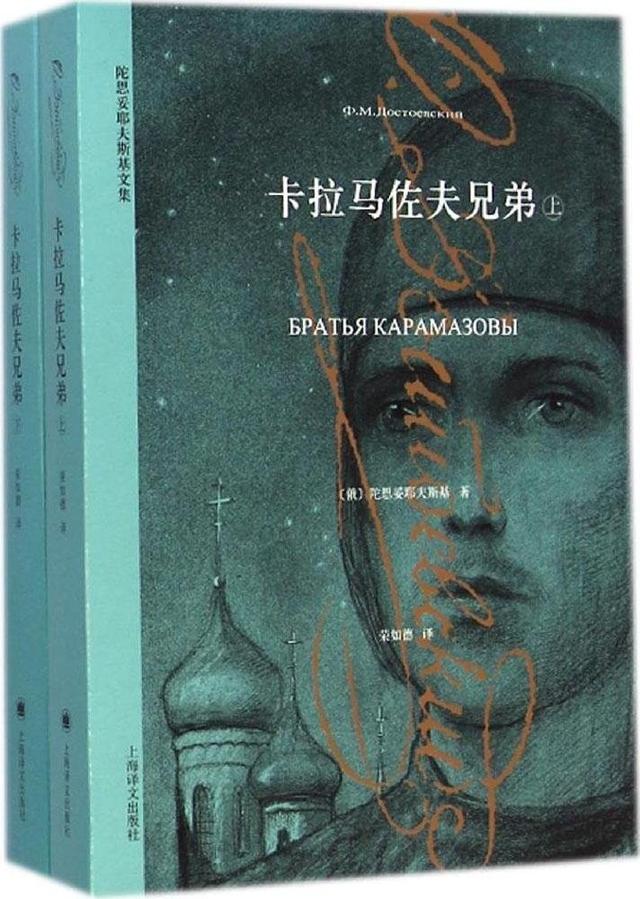
他是一个对人的内心真正着迷的作家。
现代作家的特征也是转向内心,回到自我,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现代作家的热情许多时候是给了艺术。在他们眼中,艺术上的陈旧是无法容忍的,那意味着这个作家缺乏革命性,固步自封。许多作家都说,我对生存的看法,就是我对艺术的看法。你如果要了解一个现代作家的内心世界,除了要知道他在写什么之外,还要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他的艺术方式、结构能力,常常就是他精神经验的放大或转换。
在一系列的艺术方式中,结构在小说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传统小说那种以时空为本位的结构方式,代表的是世界能够被作家所认知,世界在作家眼中是稳定的,有迹可循的,它以时间空间的正常逻辑出现;作家在世界面前也是有信心的,他能够沿着这个时空线索来探查人的存在状况。这样,结构在传统作家的笔下是以先在的时空为决定因素的,作家可选择的只是在这一结构中出场的人与事,但他不能改变大的时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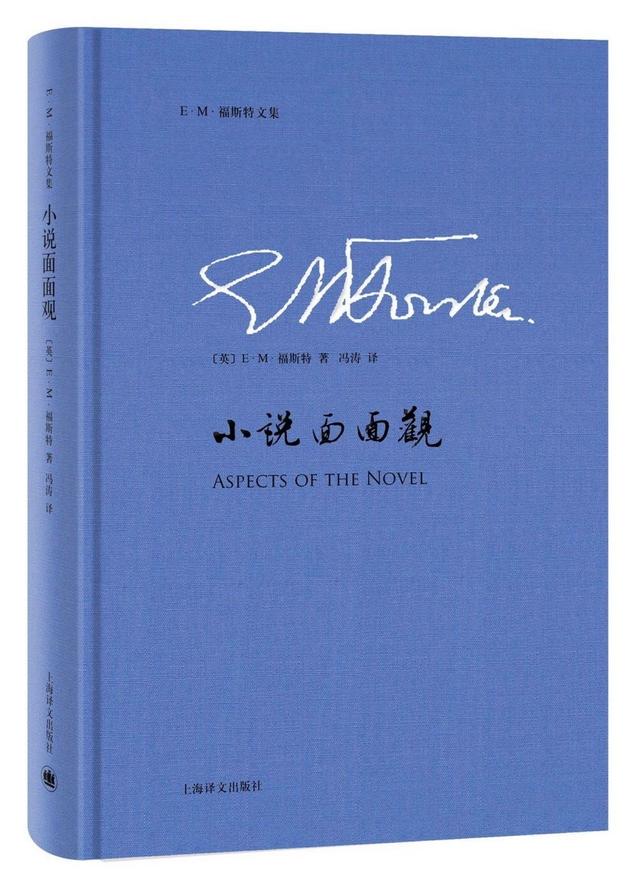
这种以时空为本位的结构形式,构成了一部小说的故事内核,同时也为阅读者进入小说提供了基本线索。这种结构方式契合了读者的固有经验,读者很容易将作家所假想的时空与自己生活的时空联系起来,并与作家维持一种简单的关系:作家是故事的制造者,读者是故事的旁观者。
二
但它很快就受到了现代小说的挑战。
首先是意识流小说,它打破了时间这一恒常的维度,让人物的意识在超时间的空间里任意往来,作家不再相信写作中假定的时间形式。
很多人都知道,时间所作用的是实体存在,而人作为一种能意识到自身是实体存在的存在,他在时间面前其实是矛盾的:他的肉体在时间里,但他的意识却是超时间的。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思维过多地受时间限制,他肯定无法写出人在时间里的冲突——有限的人与渴望无限的人之间的冲突。而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之所以能在小说中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就因为他意识到人活着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作家必须在超时间的追忆中使自己的想象力趋于无限,这就在精神向度上构成了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

这样,时间便开始折叠,尤其是它的线性特征被打破,故事结构的线性逻辑也同时被瓦解。故事成了一些记忆片断的连缀,或者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混合的地方,情节的因果关系不复存在,传统那种以情节为主体的阅读模式也受到了彻底的颠覆。
意识流小说所反对的是以时间为本位的结构模式,它表明作家不再相信时间这一未经证实的假定形式:是谁赋予了时间这一权威?我们何以相信在时间中的一切是真实的?这次革命,把写作从时间的囚牢中解放了出来,作家终于可以对时间说,我自由了。
接下来,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人发动了另一场针对空间的艺术革命。他们认为,作家在现有的空间观念里安排人物的活动,这同样有一个未经证实的前提:是谁赋予空间最初的基本法则?作家又何以让读者相信他所出示的空间是真实的?
基于此,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人都着力于描绘他们笔下那个空间,并让一个事件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反复出现,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反复叙述,力求这些人物与事件在作家眼中变得立体起来,以突破传统小说中那种单维度的平面真实。

罗伯-格里耶
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里,我们很难看到作家对某一件事的跟踪,有时整篇小说只有一道客观的视线在一些人和物上面反复移动,跟着这道视线走,我们会发现格里耶的确洞悉了空间的真相,空间成了具体的,可以触摸的了。
在这个空间里,人与物完全平等。
普鲁斯特、罗伯一格里耶等人的小说对时空的瓦解,实际上确立了新的时空观,他们也用小说证实了这种新的非线性的时空观,更接近于现代人的心灵真实。
之后,许多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基本上是以这种新的时空观来结构小说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现代主义小说从此就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模式,相反,它最重要的结构特征是对传统共同的解构,或者说,现代主义之后的大部分小说家,都无意于在小说中结构什么,它们更多的是在解构,现代主义是对传统的解构,后现代主义又是对现代主义的解构。解构的力量大于建构的力量。
三
这种解构热情深深影响了中国作家。
在中国小说还处于社会性大于艺术性的年代,一些作家开始应用解构这一武器,这对另一些作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要提到的是马原。他第一次使读者知道,小说是有一个结构模式的,而且,这种结构本身也能勾起读者猜谜一样的热情。马原将几个毫不相关的事件并置在一篇小说里,还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写作构想告诉读者,现在看来,这些手法不足为奇,一个初学写作的人都会模仿得来,但在当时的小说界,却引起了强烈震动,它使作家看到,小说还有结构这个东西。

马原
结构并不是不重要的。
这就更新了我们的小说观念:作家重要的不单是出示故事,还要看你是如何写这个故事、结构这个故事的。
马原之后,到格非的小说,小说结构的自足性就更加明显了。他的《迷舟》,使故事获得了多解的可能性;他的《褐色鸟群》,也是一篇结构感极强的小说,在时间上,这篇小说从写作时间的一九八七年进到了一九九二年,在空间上,发生在同一地方的几个事件似是而非。
格非在这里所要突出的是虚构。
虚构是一种书面的真实,我们明知小说中所发生的事实是不可能的,但格非却告诉我们,对虚构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这就是特殊的结构方式所达到的艺术效果:真实与幻念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作家一旦无法确证世界的真实,就以想象、虚构的方式来创造一种幻想的真实。这个时候,小说结构的力量就显得异常突出。
遗憾的是,虽然中国作家已经开始了对小说结构的重视,但“结构”一词在许多人那里还只是一个名词,它代表的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形式法则,是可以被解释的一个系统。这个新系统的建立,包含的主要是对传统的解构,但作家在这一系统中要结构什么呢?——这里的“结构”是一个动词。一个只解构的作家不会是优秀的作家,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在解构的同时,也出示一个自己所结构的新的艺术秩序和精神真相。

博尔赫斯
我要再次提到博尔赫斯这个人。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很大,但多数中国作家只学到了他的一些迷宫法则,并没有看到他的小说还有一种超常的结构能力。我们跟着博尔赫斯在他的小说中走动,到最后会有一种仿佛接近了无限的感觉,博尔赫斯就是以这种趋于无限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写作动力的。所以,读博尔赫斯的小说,会使我们一切俗常的阅读经验都归于无用,在他那没有出口的迷宫结构中,他出示的几乎就是一个精神异象。
尽管这个异象只是个巨大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至少对于博尔赫斯本人来说是真实的,这就够了。
作者简介: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李月)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