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些东西是要珍藏一辈子的。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会瞬间想起曾经活过怎样的日子。这些东西也许并不贵重,但它散发着我们青春的味道,散发着我们内心最珍贵的付出和保留,散发着与我们有关的人情世故,散发着岁月的幽香……
我整理了我自己,把那些曾和我紧紧相关,启发、锻炼、感悟并温暖了我人生的物和事搜集了起来,予它们以回忆的血肉,建成了“我的博物馆”。下面,我带大家走进我的“童年馆”,里面藏品很多,有几样东西构成了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我重点介绍如下——
我的“过滤嘴”裤子
先说说我们家里那一台经历了四十多年都没舍得丢弃的老缝纫机吧。这台缝纫机是我母亲的陪嫁,当时流行的“三大件”之一。母亲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生的,初中毕业考上了军校、参军到了部队。她后来成了一名军医,和我父亲是在部队里经她的领导宁永利伯伯和他的老伴儿介绍相识相恋的。当时我父亲被称为那个部队里最有前途的军官。那个年代,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婚姻模式,所以我是在这个军人家庭中长大的。

身为军人的母亲,针线活不怎么会做,拿起针线只能应付急需……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母亲在灯前踩着缝纫机给我们缝缝补补做衣裤。母亲并不喜欢做这些,经常说:“等富裕了,衣服全都买着穿!做衣服太费事了!”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布票珍贵。布票换的布,拿回来给家人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兄弟姐妹轮流穿,家里兄弟姐妹少的或者年龄间隔大的,就需要不停地改着穿。像我的这条棉布裤子,原版是我五岁时候做的,腰部是松紧带,裆很深,裤腿极肥大,奔跑时往里面灌风,可以穿四季,冬天一般套在棉裤外面穿。后来五岁以后长个子了,成了吊脚裤,母亲就坐在缝纫机前,把裤管里面窝进去的宽边放出来,凑合着长度。又过了两年,我又长个子了,实在没宽边可放,就找了一块别的什么布给拼接上,凑合着不吊脚。
有一天我去大院的锅炉房打开水,提着暖瓶经过门岗的时候,被刚换下岗休息的解放军小哥叫住:“嗨!小孩,你咋穿了个过滤嘴裤子呀?”我一愣,旁边的家属们大笑起来……
我重新审视了一下我的裤子,可不是嘛?裤子的颜色是浅咖啡色的,接上的那节是深咖啡色的,从老远看,活脱脱两根过滤嘴香烟……
我羞愧难当,一路小跑回家,脱下裤子扔给我妈表示不穿了!我妈问为啥,我怒气冲冲地跟她讲我打水被嘲笑的经过,把我妈笑得前仰后合,差点笑岔气……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申辩:“……你知道……我还挑了好几块布呢,好不容易才找了两块一模一样的,我还说看着怎么这么顺眼,哈哈哈哈……”
之后这条让人欢乐的裤子就彻底压了箱底,我妈把她少女时的军装裤拿出来裁短了给我穿,弟弟身上的裤子不论怎么接裤腿,颜色我妈一定会选好,必须不能接成“过滤嘴”的样子,但每次搬家,这条裤子我妈都不让扔,说看着就想笑,太有意思了……
多年后的某天,已经参加工作的我正在办公室忙活手中的材料,突然听到在一旁聊天的几个同事提到了“过滤嘴裤子”,我心中一惊,心想:“她怎么知道的?”于是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蹭过去和她们聊天,后来才知道,原来她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原来在那个年代,“过滤嘴裤子”的典故并不是我一人专属。
而我,因为这条新奇的裤子,不自觉地关注并喜欢上了美术。后来遇到了画家伯伯一家,学画画的热情彻底被激起,中学时专门拿出时间去学习过,高考时还去参加了提前招生的美术院校的专业课考试,后来竟然拿到了服装设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走上了服装设计的道路……
我当时曾想: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我一定会在颁奖典礼上谈起我当年的这条“过滤嘴裤子”,它是冥冥中指引我走上艺术之路的明灯;又或者,我会设计一场巨大的国际“过滤嘴香烟衣裤”时装饰品秀,请时尚大咖们前来演绎所有“过滤嘴香烟”元素的服装,把补丁做成最时尚的形态,去致敬那个难忘的年代!
铁皮盒子里的集体来信
少时不懂别离。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里出生和长大,部队大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兵入伍都是一茬一茬的,生下来的孩子也都是一批一批差不多大的。于是,我生来就有一批和我同龄的小伙伴陪伴在身边,因为父母都是军人平时忙得很,所以我两岁多就被送去了托儿所,和那些同样父母没时间带的小孩一起,天天做伴玩耍。后来上了小学,我们这批孩子又一起走进了当地著名的重点小学。我们这些从刚会说话时就结交的小伙伴们,上学、放学、吃饭、学习、考试、玩耍、打闹都在一起……这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友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也从未想过会分开。
一天,妈妈很小心也很慷慨地对我说:“我们很快要出远门,你想吃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一定会满足你。”
我想了想问:“我可以吃山楂片吗?”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从小最吸引我的就是部队大院的军人服务社里卖的八分钱一卷的山楂片。我第一次偷父母的钱就是为了去买一卷山楂片,后来被妈妈发现挨了一顿饱打,之后就没敢再提这个要求了……
“没问题!钱给你,去多买点吧,你可以去买一大袋子……”
“真的啊?!”
我高兴到忘形,忘记了妈妈说的那个前提,马上攥着钱飞奔去服务社买了一大袋子的山楂片,里面有十六卷,当场就撕开包装吃了两卷。
第二天,看到爸妈的军装上已经没有了领章帽徽,看到他们和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一起把家具家电搬上卡车,把我们的衣服都打成了包袱搬上了卡车,家里都空了……我才发觉不对劲,我回想最近爸妈经常出差,但每次出差都不带我们,怎么这次……
妈妈催促着,喊我,让我坐在卡车前排。我说:“我还要去食堂打饭呢,你们把纱布袋子放哪里了?”妈妈突然鼻头一酸,把山楂片塞进我手里,说:“不用打饭了,慢慢吃,后面路还长着呢……”我被大人们赶着上了车。
车子开动后,从车窗里掠过了我熟悉的家门、我小伙伴们的家、部队的大礼堂、我的皮筋绑过的树、我的小学、我熟悉的大街、城中的小河、郊区的山林……直到所有熟悉的东西全部消失,我惶恐不安起来,突然间崩溃大哭……我觉得我出卖了自己,用一袋山楂片做代价遗失了我所有的一切……
那一刻,我懊恼非常!
我哭着向我爸妈喊:“我再也不吃山楂片了,咱们回去吧!我明天还要上学呢……”
那天,山楂片酸酸甜甜的味道,只剩下了酸,酸到了心里,又从我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回到了嘴里变成了咸的和苦的……
那些陪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我甚至比亲人更需要他们、更爱他们、更想念他们……
那年,父母转业到地方后,我转学到了新环境,一直不适应,一直怀念过去的伙伴们。
大约过了两个月左右,有一天,妈妈回来神秘又高兴地说:“你猜我给你带什么了?!”
看着她,我沉默不语。
她说:“你猜猜,猜猜看!”
我说:“不知道,没什么高兴的。”
她转身把一个大包裹塞给我:“看看!惊喜吧?”
我一看,熟悉的学校名字从邮递单上弹跳进了我的眼帘——
“是……是、是……”我结巴着。
“是呀!就是呀!你的整个班都给你写信了!”妈妈看着激动到手足无措的我说。
我们激动地满屋子找剪刀,然后颤抖着手、小心翼翼地把邮政包裹打开,取出了全班三十九位同学和老师写给我的信。那个晚上,我又哭又笑地把它们看完,大家的想念和鼓励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熟悉的集体中,让我重新找回了安全感。我记得小伙伴姜丽还给我画了一幅以当地标志景物为背景的风景画,那是我们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这些信是一颗颗我熟悉和了解的、爱我的心,是我最纯真的情感记忆,我把它们收藏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每当想念同学和老师了,就拿出来读一下,一遍一遍的,陪我度过了小学最艰难的转型时光……
亲人是上天派给你的朋友,
朋友是你在世间为自己找的亲人。
——这是一位清华学子在中央电视台《交换空间》栏目中写给他挚友的话,被我铭记,镌刻在了“我的博物馆”的展墙上。
保姆奶奶床头的照片
在我小时候,保姆换了好多个。
在我去托儿所之前、弟弟出生之后,家里都需要有人照顾小孩。父母当年都是离开故乡去参军的,身边没有老人,家务让人分身乏术,只能把我们托付给保姆。
在我们家工作时间最长的保姆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单身奶奶,她没有孩子,自三十多岁守了寡,一直单身到成为我家的保姆。保姆奶奶十分要强,非常能干、重情义,在邻里间口碑极好。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青色大襟褂子,干干净净的,忙里忙外。有她,家里总是整洁有序。她经常月初从母亲手中接过工钱,月末我家里没钱了,她又重新把钱塞回到母亲手中……很多时候,她都是自掏腰包给我们改善伙食,有时还带我和弟弟去早市吃油炸糕解馋。我们一直有种错觉:她就是我们的亲奶奶。
直到有一天,她跟爸爸妈妈说,弟弟该上小学了,她完成了使命,应该离开了,不能让我们家再花冤枉钱请她……
这些话招来了我们全家的极力反对!大家都表示不能接受。六年了,我们早已习惯了生活中有这位老人。妈妈和爸爸动情地表示:他们从小离家出来当兵,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早已将保姆奶奶视为自己的母亲,这么多年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老人孤苦伶仃,没家没归宿,我们可以给她养老,给她送终,把她当成亲人一样,大家有钱没钱都一起过,请她不用多想,留下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老人固执地说什么也不同意,她想自力更生,她不愿意被豢养,更不愿意增加我们的负担……于是,在开过几次家庭会议之后,父母决定:给保姆奶奶找个老伴儿!
于是,在多方托人物色之后,父母为保姆奶奶寻觅了一位刚丧偶的离休老干部。这位老干部生活在长岛,人非常厚道,家里的孩子也都很孝顺。于是,在征得了保姆奶奶的同意后,我爸妈积极撮合,把保姆奶奶像嫁亲人一样嫁到了老干部的家中,他们家的儿女也像迎接亲人一样把保姆奶奶迎到了自己家中……这在当时,在当地,是轰动一时的新闻。那天,我作为保姆奶奶的“娘家人”,穿上了鲜艳的新衣服,也第一次看到保姆奶奶脱下了青衣大襟褂子,穿上了大红色的绸袄,第一次看到她那慈祥的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光……
十五年后,我已经长大,爸妈得知保姆奶奶的老伴去世了,已经转业到其他城市的我们长途跋涉,去长岛探望她。
到达后是一个清晨,老干部的孩子们真诚地去码头迎接我们,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告诉我们保姆奶奶的近况和平时的作息时间。他们怕早告诉奶奶,她会焦虑地一直盼望着,所以在估计她晨练回屋以后,才让孙女带我们去了奶奶家。
推开门,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奶奶惊呆了!她不敢相信是我们,她使劲搓了搓眼睛确认后,激动地喊:“蕾蕾啊!蓬蓬啊!是你们吗……”
我们上去使劲地拥抱了奶奶,大家的眼里都泛着激动的泪花……
我们拉着她的手,和她激动地聊起了家常。其间,我发现了在奶奶的床头上,挂着两个小镜框,一个里面是她老伴的照片,另一个里面是一位不认识的老年妇女的照片,这个让我很惊讶。
等大家都去筹备午饭了,我问奶奶:“这位老奶奶是谁?”
她说:“是我老伴儿的亡妻。”
我惊讶不已,问:“为什么要挂她的照片?”
她坦然一笑,摸着我的头说:“一直都挂着,她是孩子们的亲妈,拿下来,孩子们会伤心。我也感恩哪,他们接纳我一个孤老婆子,让我的晚年过上了好日子,老天爷给了这么多孝顺的孩子在身边,我知足啦……”
我们离岛两年后,保姆奶奶安详地去世了,她的继子女们按照当地风俗,给奶奶隆重地办了后事,据说出殡当天,他们披麻戴孝哭得像泪人……
事后,她的继女给我妈妈打来电话,哭着说:“我们最后一个妈妈也走了……”
空空的一铁盒擦手油
“童年馆”的馆藏,我和我父母核实过,大多他们都记得,也都认可,尤其上面写到的几件馆藏和与之相关的记忆。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我妈反应特别大,她强烈反对!说事情是有,但时间上不对!说我是在瞎扯!但那件事,那个瞬间,却是我一生无法治愈的渴望。
我在上幼儿园之前上过托儿所(这件事我妈坚决否认,说她绝不会把那么小的我送到托儿所),我被“全托”很长时间(这我妈也坚决不承认,说没有全托过那么长时间)。好吧,我按照我自己的记忆来描述吧,因为这个存在对我一生影响深刻。“全托”的意义是一周或者一个月(有特殊事情的时候),其间只有一天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其他时间都全部在托儿所中度过。于是,小小的我特别特别盼望这一天,盼望我妈妈来接我。
我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爸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们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才来接我一次?”
阿姨说:“不是,他们太忙了。”
我说:“我怎么样做,他们才更喜欢我?”
阿姨说:“你现在刚洗完手,再抹上擦手油,香香的,他们就喜欢你了……”
周六傍晚,我妈妈来接我之前,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擦手油全部抹在了脸上……

阿姨见到我,惊讶得看我的眼睛都斗到一起了:“一盒呀!啊?我的天!全抹脸上啦?像个油猴子……”阿姨想拿手绢帮我擦擦,我躲着不让,她每次靠近我的时候,我都低下头或者转过脸去,不愿让她碰我的脸……阿姨突然理解了,她拉着我的手沉默了好久,用很温柔的声音告诉我,我妈妈快来了……
焦急不安又漫长的等待后……
我妈妈来了,她好像是披着阳光斗篷进来的,开门的那一刹那,我迎着光朝她张开了双臂,她抱起了我,问:“这脸上怎么抹了这么多油?”
阿姨帮我说:“她想香香的,美美的,让你喜欢她,早点带她回家。你瞧,这一盒子的擦手油全给抹脸上了……”
妈妈没说什么,把老师递给她的放擦手油的空铁盒放进军装口袋,抱着我,离开了。
以后的日子,生活没有因为我脸上抹了一盒子的擦手油而改变,我依然是那个生活在托儿所,期待迎着阳光、张开双臂,等着家人抱起我离开的小姑娘……
很多年过去了,托儿所的事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是时常会想起那个瞬间,抹了一铁盒子油的脸,迎着阳光、张开双臂,奔向我爱的人……
二十年后,我离开媒体进入了民政系统工作,当时正值儿童福利院进行创新业务探索,开启了“孤残儿童助养”的新模式,我成为北京市第一位正式签署儿童助养协议的助养人。我助养的儿童是一名一岁半的小男孩,他是出生的当天被遗弃的,是在儿童福利院“土生土长”的孩子……
我每周五下班后去接他,周一早上再把他送回儿童福利院(有接送班车停在民政局门口)。小家伙当时刚学会走路,我第一次要把他领回家时他怯生生的,很害怕,头一直低垂着,任我怎么逗他都不笑,甚至在离开的时候他崩溃得大哭起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熟悉了以后,他开始慢慢信任我和依赖我了,睡觉的时候也会悄悄抱着我……
有个周五,我早早结束了手头的工作去接他。他看到我后高兴得大叫起来,两眼放光,从一群孩子中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高高地举起了双臂,夕阳洒在他仰起的小脸上,那充满了惊喜和期待的眼神瞬间刺痛了我——那一刻,窗外照进来的夕阳之光像一道闪电,击穿我的身体我的心,射向我已经沉封在记忆深处的那个瞬间……那一刻,我被一股巨大的酸楚击中,这酸楚一直冲到我的鼻尖,我眼前闪现出当年的那个抹了一脸油的自己,那无限信任、无限憧憬的眼神,和高高举起迎向我妈妈的双臂……
抱起他时,我紧紧地抱住他时,我好像也抱住了那个小小的自己,我的感伤瞬间瀑出了眼眶……
挂在我脖子上的钥匙
小时候放学后我经常玩疯了,和一群小伙伴翻墙爬树,钻防空洞……经常是大人满院子喊“吃饭”,或者直接找到我把我从小伙伴中拽出来,才能结束我的玩耍状态,回到饭桌上。
爸妈下班比我们放学晚,家里就只剩保姆奶奶,遇到她出门置办东西,或带着弟弟出去遛弯儿,我就进不了家门。
最初,大人们给我配了家门钥匙,但我觉得带着钥匙玩耍十分不方便——跳皮筋时,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打脸;放兜里吧奔跑翻滚时又经常蹦出来;把钥匙绳拴在裤鼻儿上,系上死疙瘩,有次绳断了,钥匙也没了;放手里攥着上墙爬树的又掌握不了平衡……钥匙对我来说真心是个累赘!在把钥匙弄丢过几次后,我就索性不带了,进不去家门就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只安心等着家长“叫吃饭”……

但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在我小学一年级时就画上了句号。
一天黄昏,妈妈喊我回家吃饭。但那一天,我明显感到她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和平时不同。妈妈领我走到路的转角,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她停了下来,蹲下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布条编好的绳穿着的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诧异地看着她:“我不要这个!”
我握住钥匙正想摘下这个束缚,妈妈压住了我的手,很郑重地对我说:“以后,就这样带着,不要摘下。”
我被这种凝重震慑住了,说不出话来。
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要去老山前线打仗了,两人都已经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可能很快就要出发。
“那不去不行吗?!你们为啥都去呀?!”我带着哭腔喊。
“不行!我们都是军人,随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保卫祖国是我和你爸的本分……”
妈妈那天跟我说的话并不很多,但总是停停顿顿,经常是说一句,沉默好久,再说一句,又说不下去了……
妈妈最后交代:“听保姆奶奶的话,你是姐姐,爸爸妈妈不在,要照顾好弟弟!”
那个黄昏,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生离死别”。
后来,因为父母不在同一个部队,两边的领导在核查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我们是双军人家庭,还有两个孩子,都很小,两边也没有老人跟随照顾,就不约而同地没有批准他们去前线。
替补妈妈出征的,是她们医院里一位年轻的军医——小韩叔叔。
小韩叔叔二十出头,方圆的脸蛋,稚气未脱,有时说话还显得羞涩。我以前去找妈妈时,经常看到他,还经常和他打招呼、玩耍……
部队出征后,学校让大家自愿给老山前线的战士们写信鼓劲,说会有后勤保障人员统一送到前线去,当时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我也提起了笔……
一年后,小韩叔叔从老山前线凯旋。作为英雄,他被邀请到我们学校做报告。进场时,我惊讶地发现,被大家簇拥着进来、身上挂着军功章和大红花的小韩叔叔竟然是拄着双拐来的,他的一条腿没有了……
小韩叔叔被大家扶到主席台中央坐好,他的眼神里已没有了天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他身上的军装极为相称的坚定和沧桑,笑的时候却让人感觉到一种隐隐的痛,他的面庞苍老稳重了许多。
在主席台上做报告时,他说他收到了我的来信,还说出了我的名字,说他记得我,是同一所医院里一个大姐的孩子。他说我写给他的这封信很短,但给了他亲人般的感受,给了他战斗的鼓舞,和活下去的希望……
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有些脏脏的、破了边角的、我给他的信,读了起来,几度哽咽……
我在台下不敢看他的眼睛,直到他读完,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些同学还扭头看我……而我此时,却用双手捂住了脸,失声痛哭起来……
他们不知道,我写那封信最初的冲动,是写给我爸爸妈妈的……
他们更不知道,如果小韩叔叔不去前线,今天拄着双拐坐在台上的,可能是我的妈妈……
妈妈在小韩叔叔回来后,看到小韩叔叔的现状非常痛心,她除了关心小韩叔叔的身体,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积极为小韩叔叔张罗相亲对象上。走到哪里,她就把小韩叔叔的照片带到哪里、夸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她总能几句话后就把话题绕到人家亲戚朋友里有没有善良热情、心肠好的姑娘这件事上……
只可惜,直到我爸妈转业离开部队,小韩叔叔还孑然一身。
我的童年结束在那个挂上钥匙的黄昏——我常常这么想。
十年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名叫《和平年代》。它最后的一句话像用刻刀沾血一般篆刻在我心底: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

盛 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老舍文学院高研班学员。曾工作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单位,从事记者、导演、主持人、频道监制等职业。自初中起在《人民文学》《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部分结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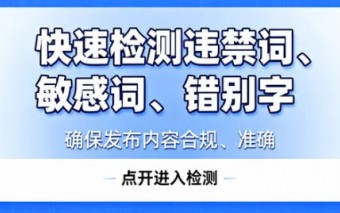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