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堂课上,“大老师”和“小老师”配合教学。
一堂课上,“大老师”和“小老师”配合教学。
她是一名袖珍人,在郑州康达能力训练中心做助教,帮助自闭症等特殊儿童做康复训练。平日里备受歧视的身体特征,成了被特殊儿童接纳的优势,使她能以玩伴的身份,在课堂上做正确的示范,并帮助主教老师调动气氛。
在训练中心,这些助教又被称为“影子老师”,项目启动至今7年,累计近50名袖珍人在此工作,目前在职的有12人。他们中的多数都曾因为身高而求职艰难,或者自卑地躲在家人的庇护下,直到遇见这些特殊儿童,才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用赚来的钱打激素增高,还是就这样陪孩子蹦蹦跳跳?40多岁后,一旦身体迅速退化,又将何去何从?
文|陈怡含 图|吕萌
 课间空闲时,“影子老师”留在教室里学习自闭症儿童陪护的相关知识。
课间空闲时,“影子老师”留在教室里学习自闭症儿童陪护的相关知识。
学生中的“卧底”
网红儿歌响起,教室的特制地板出现明显的震动,娜娜拉着几个孩子绕着教室转圈。打头的男孩穿着蓝色马甲,后面的孩子都在和娜娜对视、互动,他却神情恍惚,四处张望,不时吐几下舌头。娜娜一松手,他便不再前进,在原地挠着头。
这堂音乐游戏课正要开始,年轻的女老师组织大家搬来板凳,8个“小朋友”坐成两排。实际上,只有前排的4个是学生,剩下的是“影子老师”。
 “影子老师”协助孩子们参与音乐游戏课程。
“影子老师”协助孩子们参与音乐游戏课程。
娜娜负责的正是蓝马甲男孩,今年4岁,两个月前刚入学时,总是躺在地上哭,连简单的跟随都做不了。他还不会表达上厕所的意愿,有时会把屎尿拉在裤子里,都是娜娜收拾。这天,他直接在教室脱下裤子,娜娜眼疾手快,一把提起裤子,带他跑去厕所。
有时,男孩好像突然切换回了自己的世界。玩响鼓时,老师让大家敲击,他却自顾自地摇晃;大家在做体感游戏时,他会突然跑向投影的幕布,靠着放空。每到这时,娜娜需要提醒他,或者和主教老师,也是大家口中的“大老师”一唱一和,做出正确的示范。
 “影子老师”引导孩子完成游戏动作。
“影子老师”引导孩子完成游戏动作。
音乐游戏课之后是小组课,以集体游戏为主,穿插简单的问答。还有两位“影子老师”和娜娜一起上课。一位最为娇小,身高约一米一,两岁左右的孩子,经常分给她带。另一位则最为年长,今年39岁,与其他“影子老师”相比,脸上已经有些中年人的模样,但双手的皮肤还像孩子一样细腻。
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丢手绢,他们和“大老师”相互配合,让每个学生得到适当的锻炼。有时候,要跟自己的学生说悄悄话,引导她丢给水平相当的小朋友。学生跑摔了,他们会故意多跑一圈,让学生抓到自己。女孩不爱丢给男孩,也靠他们在中间创造机会。有人说,这些“影子老师“就像安插在学生中的“卧底”。
 娜娜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娜娜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这家训练中心成立的最初几年,课堂上还看不到袖珍人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第一批学生多是智力障碍儿童,不久后,逐渐接收自闭症儿童,目前是郑州乃至河南省最大的一所针对自闭症、语言障碍、学习困难、脑瘫等特殊儿童进行综合性康复训练的基地。
主任岳亚非说起,首个入职的袖珍人是洛阳师范学院的本科生,因为身高,找工作屡屡受挫。他看到报道,认为此人的学历、形象和能力都很优秀,便招了进来。
通过她,岳亚非接触到更多的袖珍人。2013年,当地的袖珍人艺术团开了间西餐厅,他常去捧场,但不到一年,餐厅就倒闭了。后来,20多名袖珍人几乎都成了待业者。
那时,训练中心的管理层探讨出一个方案:这些人的目光和孩子是平等的,能不能请他们来,做孩子的小老师?于是,他们在团里招募了五六位有意愿的袖珍人,开始自闭症康复教育的上岗培训。
起初,也有家长不认可,课上了没几天,就要换掉“影子老师”。并非老师做得不好,只是“看着不舒服”。岳亚非劝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作用。他仿佛感知到家长的潜台词:“我的孩子本来就有缺陷,你们还要再安排一个残疾人过来?”
 教室外,家长们紧盯监控屏幕,看孩子们上课。
教室外,家长们紧盯监控屏幕,看孩子们上课。
大约过了一年,质疑声慢慢消失,家长对“影子老师”的需求量增长了很多,项目也得到残联领导的表扬,被称为“以残助残”的典范。训练中心认为试点很成功,开始招收新的成员。
娜娜就是被第一批老师介绍过来的。2014年入职至今,她接手过上百个特殊儿童。有的洁癖严重,鞋沾上泥就要死要活,洗净之后也拒绝穿,雨雪天直接向学校请假,就怕踩上泥巴;有的存在刻板行为,从家到学校的路线、方式必须固定,有天临时改乘出租车,便要大声哭闹。在她和“大老师”的帮助下,这些孩子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如今,她已经算得上一位成熟的特教老师。3个月前,中心18周年校庆,她被评为年度优秀教师,是唯一获奖的“影子老师”。冬天是中心的淡季,许多外地的孩子受不了郑州的气候,回到老家,第二年春天再来康复。即便如此,每天的9节课,娜娜总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提高孩子们在集体活动中的表达能力,老师们让他们坐到教室中央,带领大家做动作。
为了提高孩子们在集体活动中的表达能力,老师们让他们坐到教室中央,带领大家做动作。
一个平等的机会
“影子老师”是娜娜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早年间读技校,能接纳她的专业寥寥无几,父母替她选了幼师专业。她只能上文化课,舞蹈课的老师觉得“动作有危险”,钢琴课的老师说:“你的手根本够不到八度(琴键上的音程距离),就不用学了。”
勉强毕业后,因为自卑,她整日待在房间,漫无目的地看电视,除了吃饭,几乎不踏出房门。这种低迷的状态持续了至少半年,姨妈看不下去,把她接到家里,请她帮忙接送儿子。
她被推着走入社会。起初,接送表弟时,老师会因为身高而质疑她的身份,她不怎么解释,反倒是表弟出面维护,说姐姐是个大人,什么都会。久而久之,老师了解了情况,会当面表达认可,并鼓励她找工作。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表弟毕业后,她先后在姨妈的药店和舅舅的服装厂做过活。她觉得,这些都不算工作,只是给家里帮忙。在服装厂,她没有正式岗位,哪批衣服赶不完,就去哪个组支援,陪他们加完夜班,白天睡到自然醒。工资直接给到母亲,她也没什么意见。
她曾短暂地有过去北京打拼的念头,那里有个袖珍人皮影剧团,看了剧团的照片,她心动了:“妈呀!世界上除了我,还有别人也这样。”但父亲不许她去:“那么远,人家给你装麻袋里,一背就走了。”她吓得够呛,打了退堂鼓。
 娜娜和小伟。
娜娜和小伟。
后来,她和同是袖珍人的小伟结了婚。两人在县城开了间手机维修店,客户的信任很难积累,有人看到店里只有两个“小人儿”,扭头就走。
应聘“影子老师”,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勇敢出走。她没有告诉父母,直接在马路上拦了辆大巴。没过多久,在郑州打工的表哥接到家里的命令,出现在中心门口,声称要把她锁进宾馆,次日送回老家。她坚决不从,难得遇到一份“身高是优势”的工作,怎么也要尝试看看。
几天后,佳佳坐了27个小时的硬座,从哈尔滨来到郑州,和娜娜搬进同一间宿舍。她的出走也遭到父母的反对,母亲甚至放下狠话,说要死给她看。现在提起,她仍会落泪。
与娜娜不同,她很早就渴望跳脱家人的庇护,真正自食其力。但现实很残酷,她找了几个月工作,每三五天扫一次街,前台、收银、服务员,都是门槛不高的活,却从没应聘成功。多数时候,拒绝的理由很委婉,比如“我们已经招到人了”,或者“我不是老板,说了不算”,也有不留情面的,叫她“赶紧回家找妈妈”。
后来,她只能去翻小广告,找些在家做的活。她刷过单,串过头饰,也做过游戏代练。父母希望她到了年纪,找个合适的人嫁了,只有弟弟支持她,觉得那样的人生太无趣了。
她一直在等一个平等就业的机会。直到2014年,一位袖珍人网友推荐了“影子老师”的项目,她觉得机会来了。
 与特殊儿童相处时,袖珍人的身高是一种优势,可以和孩子平视,有一样的童声,孩子们会更愿意接近。
与特殊儿童相处时,袖珍人的身高是一种优势,可以和孩子平视,有一样的童声,孩子们会更愿意接近。
陌生的羡慕
娜娜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入职第一天的忐忑。这里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有的会随地大小便,有的会躺在地上打滚,有的生起气来,会故意磕自己的头。那时的娜娜对他们不甚了解,和多数普通人一样,有不解,也有惧怕。她想,我干得了吗?有些孩子比我还高,万一给我一巴掌,不得把我打晕了?
她的第一个学生只有两岁多,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但除了“妈妈,吃糖”,其他什么都不说。家长说,原本孩子的语言功能是正常的,一年前遭遇车祸后,出现应激反应,不再说话。
“大老师”告诉娜娜,要做个“先知”,提前预测学生的想法。他喜欢画公鸡,娜娜就要提前准备好纸笔。同时,要像电视剧的旁白一样,描述他的心理和动作。“我要拿画笔,我要画公鸡……”娜娜每天帮他配上大量“旁白”。一个月后,他突然开口说,自己想要某个玩具。
家长高兴坏了,不停向娜娜道谢。她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对这个社会有用:“除了家人,也有别人能认可我。”
 娜娜用手机录制着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便于下课后和家长交流孩子当天的进步。
娜娜用手机录制着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便于下课后和家长交流孩子当天的进步。
从前她总在想,为什么世界上有我这样的人?小升初时,明明录取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初中的老师却不相信,说她跳级跳得太快。她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回家和母亲哭诉。后来她四处去开证明,直到开学一个星期,才坐进教室。
学生时代,言语暴力一直围绕着她。小时候懵懵懂懂,没有受到太深的伤害,到了初中高年级,她的心智逐渐成熟,越发在意那些冷言冷语。她开始有了报复心理,不再认真学习,每天混日子,打不过那些嘲讽自己的同学,就瞄着他们自行车停的位置,一下课便跑出去,挨个把气门芯拔掉。
佳佳读初中时,也曾受到同学的羞辱,“特别是男生,要不弄个毛毛虫,要不揪你头发”。她反抗的方式是使劲学习,后来,三门主课的老师都选她做课代表,那些羞辱她的同学,全跑来借她的作业抄。
她们都曾觉得,命运对自己最为不公。成为“影子老师”后,面对众多特殊儿童,这种想法被动摇了。
 在做康复训练的儿童。
在做康复训练的儿童。
有位八九岁大的唐氏综合症患儿令佳佳印象颇深。这个男孩在中心训练了四五年,很多“影子老师”都带过。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得知他的病情,决定离家出走。后来父亲再婚,生了个健康的宝宝,也不再管他。几年来,他的衣食住行全靠奶奶照顾,父亲偶尔打些学费,多数时候,奶奶靠拾废品补贴家用。如今老人70多岁了,每天送孙子来做康复,走路都颤颤巍巍,孙子躺在地上耍赖,她也拉不动了。
曾有家长对“影子老师”说,宁愿孩子和他们一样,虽然不长个,起码能照顾自己、养活自己。这种陌生的羡慕,带给他们的不是快乐,而是心酸。
 孩子们学习相互分享食物。
孩子们学习相互分享食物。
他们懂得被异样目光注视的感觉,因此对学生投射了更多同情。每次提起学生,娜娜总是避免提及自闭症、脑瘫等字眼,只说这个语言弱一点,那个肢体弱一点。有次,一位记者问她:“如果给你一个自闭症小孩和一个袖珍人小孩,你选哪个?”她深感冒犯,当场怼了回去:“你去问我们领导吧!”
袖珍人很难生育,中心的教务主任问过不少“影子老师”,是否有意愿领养孩子,没有一位给出肯定的答案。他们都说,不愿把自己受过的压力传递给下一代。“我们不领养,会有更好的人把他们领走。”
在岳亚非眼里,有时,他们会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位“影子老师”曾每天扶着学生上下楼梯数十次,后来手腕长了脂肪瘤,确诊后,他什么要求都没提,换了只手,继续扶着学生练习。后来,学生每次在午睡时醒来,都会钻到他的被窝,抱着他的脖子,用很纯洁的眼神看他,“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几位女老师的小群里,到了放假,有人会发,想我家谁谁了,其他人便回,谁家没有似的。
 “影子老师”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孩子完成同样的动作。孩子们趴下,他们要跟着趴下,孩子们在地上躺着,他们也要跟着做。
“影子老师”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孩子完成同样的动作。孩子们趴下,他们要跟着趴下,孩子们在地上躺着,他们也要跟着做。
放弃长高
一天的课程结束,娜娜和丈夫小伟打扫完教室,骑着电动车回到出租屋。路程不远,5分钟就能骑到。小伟养了十几条孔雀鱼,回家后,来不及脱掉羽绒服,便跑到鱼缸前喂食。
几天前,他们刚刚搬进这个40多平米的开间,行李还没收拾妥当。网购的家具和装饰品还在配送,吃饭时,娜娜在泡沫塑料上垫了个抱枕,试探着坐下去,开玩笑道:“不会撑不住我吧?”
 小伟回到家中。
小伟回到家中。
他们决定不在郑州买房,尽可能地享受生活。去年,两人用攒下的几万元买了辆国产车,平时停在中心门前的免费车位,假期时叫上其他“影子老师”,自驾去近郊游玩。
娜娜对现状比较满足,觉得“挺安逸的”。相比几年前,她放下了一些执念。
来中心工作的第二年,她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以后挣了钱,再去注射能让自己长高的生长激素。她去医院咨询,得知骨骼尚未闭合,还能打针。但医生说,打针就像化肥催熟,在长高的同时,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等问题。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打针,尽量在家养着。
 游戏结束后,老师们为表现出色的孩子戴上头花,以示鼓励。
游戏结束后,老师们为表现出色的孩子戴上头花,以示鼓励。
娜娜曾非常渴望长高。小学三四年级时,父亲带她来郑州看病,医生直白地说:“你们家的一百元钱能垒多高,孩子就能长多高。”那时,一针生长激素一百多元,一天一针,一个月就要花费三四千元,比北京每平米的房价还高。娜娜的父母以务农为生,收入不高,这个数字是全家大半年的花销。
父女俩面面相觑。如果年龄再大一些,娜娜会因为家里的条件而放弃打针。但那时的她“觉得自己真的很小”,一次,医生说她有90厘米高,她没有概念,跑去问父亲。父亲拉开卷尺,比一只胳膊长不了多少,带给她很大冲击。
她想打针。父亲留下回家的路费,剩下所有的钱换成26针生长激素。26天后,药用完了,他们回到老家,决定攒了钱再来。父亲比着她的头顶在门沿上画了一道,说她长高了些,她很开心,也没计较长高多少。“现在想想,我爸每年都画上去一点点,长没长高也不知道。”
 音乐游戏课上,孩子们和“影子老师”互动。
音乐游戏课上,孩子们和“影子老师”互动。
那位最娇小的“影子老师”,也曾为长高付出很多代价。她从5岁开始求医,从老家到省会,再到北京,父母借钱带她四处奔波。每次检查至少抽5管血,有时抽得晕了过去,“医生给个白药片,吃了才好一点”。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个“药罐子”。只要宣称能长高的保健品,父母都会买给她吃。家里的写字桌用厚玻璃压着各种广告,安利、生命一号、太阳神、21金维他……花了不少钱,却没见到成效。
如今,她和娜娜都放弃了打针。她们想要维持这种能蹦能跳的生活,继续陪着中心的孩子,直到干不动的那天。
 “影子老师”更像是特殊儿童的哥哥姐姐,陪伴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影子老师”更像是特殊儿童的哥哥姐姐,陪伴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娜娜说,袖珍人的退休年龄会早于普通人:“别看我们现在像个小孩,到了一定年纪,身体退化得很快。”只是眼下她还无需焦虑,“再干10年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那位39岁的“影子老师”,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奢侈。从前,中心有对比他年长的袖珍人,男的45岁,女的41岁。近几年,他们的体力明显跟不上了,女老师还在抬玩具车时扭伤了腰,落下病根。今年复工后,他们便辞了职。校庆时再见面,女老师甚至连走路都有些艰难。
他们希望一直守着,学生则是来往不停的。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生毕业了,就不要再联系。彻底脱离老师的帮助,才算真正成功。如果突然联系老师,可能意味着情况出现了反复,需要再做康复训练。
娜娜保留着很多家长的微信,但很少找他们聊天,只会默默在朋友圈里寻找学生的动态。最近,她看到去年带的一个轻度脑瘫的男孩,在老家读了新的幼儿园。“乖乖,走了就不要再记得老师了。”
 户外实践课上,“影子老师”牵着孩子们走在街头。
户外实践课上,“影子老师”牵着孩子们走在街头。
(编辑:映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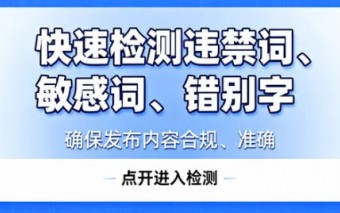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救命的医疗设备,如何沦为个人提款机?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原价上千元“贵妇霜”网店卖不到百元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花20多万元就能买到“铁饭碗”?起底涉案金额超8000万元的特大招聘诈骗案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
直播带货,热闹下的烦恼咋消除